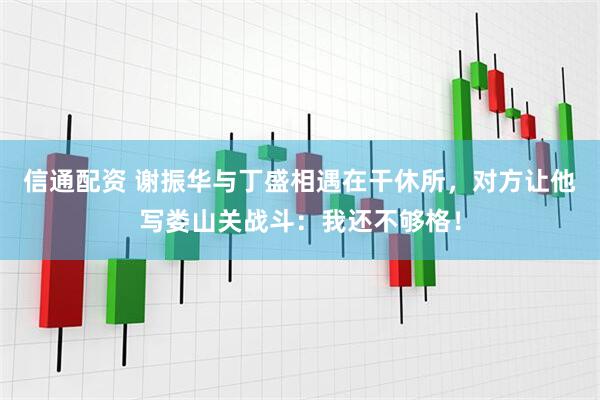
“老丁,你还记得娄山关吗?”——1994年春天,昆明疗养院的走廊里传出一句略带笑意的招呼,声音不高,却让屋里的人几乎瞬间从思绪里被拽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枪林弹雨。丁盛抬头信通配资,看见推门而入的谢振华,一时间竟有几秒没反应过来。
两人上一次正式见面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。此刻重逢,谢振华是离休的大军区正职,丁盛只享受师团级待遇,身份差距拉开得有些尴尬。不过军装脱了,年岁添了,战场上留下的默契却没有磨平。丁盛起身,敬了个标准军礼,谢振华摆手:“别来这一套,坐下聊。”
话题很快绕到娄山关。那是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最惊险也最提气的一仗,丁盛当时只是红三军团十二团连指导员,谢振华担任营教导员,上下级配合却一拍即合。术业有专攻,谢振华负责政治鼓动,丁盛临阵组织火力,双方硬是带着一个营撕开了黔北的防线。多年后提到这段经历,两人不约而同先想到的不是“战术成功”,而是“怎么活下来的”。
时针拨回更早。1929年,二十二岁的丁盛在家乡湖北罗田参加红军,递上报名表时,他没想到自己在未来二十年里几乎从不按常规路线升迁。到1933年才当上班长,此后调到王稼祥身边做警卫,因表现稳当被推荐进黄公略高级步兵学校。学成归队不久,中央苏区传来大转移命令,丁盛从后方直接补到红三军团前线,这一步让他躲过了反“围剿”中的大清洗,却把他推到长征最血腥的地带。

与此同时,谢振华早在1928年就已担任连指导员。他家境贫寒,读书不多,演讲却有感染力。红军里有人评价他:“说起话来,连夜里巡逻的战士都能打起精神。”1934年冬,他随军进入贵州北部,负责整编零散部队。到娄山关前夜,他手头只剩下不足一个营,但士气极高,“想跟着教导员拼命”成了大家嘴边的话。
1935年1月15日凌晨,天刚蒙蒙亮,娄山关外浓雾盖山。先头两个连摸到山脊线时,国民党黔军反击部队一个团已就位。战场极窄,能展开火力的地段不足两百米。营里早年用惯“猛冲猛打”的战法,这回却被地形逼得改走“贴坡蠕动”。谢振华见状,干脆让丁盛带一个排沿侧翼迂回,自己在正面用手榴弹掩护。不得不说,这一招凑效:突击排先上到山坳背后信通配资,打乱敌纵队指挥链。雾散时,娄山关已插上红旗。
打完仗不到三小时,丁盛肩胛中弹,鲜血浸透棉衣。医疗条件有限,他被火速送往卫生连,随后调到红三军团十一团任指导员。那阵子他常半夜疼醒,一伸手摸到裹得像粽子的伤口,心里却念着一句老话:“活下来就是本事。”正是这股劲,让他在八年抗战里从政治处股长一路干到团政委。
解放战争爆发,丁盛被从政治岗位“硬拉”到军事主官的位子上。吉黑平原的冬夜,他第一次以纵队副司令身份统一指挥几个旅,从此在四野打出了名气。1949年底,少将名单尘埃落定,他成了第二位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的少将。谢振华的履历则更稳,1982年出任昆明军区政委,三年后主动退下,挪给年轻干部机会。外界评论他“官到顶峰不恋栈”,其实他自己说得直白:“新兵想冲,老兵让路。”
说回1994年那场对话。老营教导员指着丁盛:“回忆写一下娄山关,很有必要。”丁盛摆手:“那阵我只是连指导员,不够格。”谢振华笑:“你不写,谁写?现在能完整记住经过的,也就剩咱俩。”昆明日报的编辑随后登门,丁盛依旧婉拒,只留下一句话:“我写不了全局,怕误导后人。”

这种推辞听上去谦逊,细想却有另一层用意。娄山关战斗是长征中为数不多“一仗打开,一仗巩固”的典型,涉及统帅部的整体部署,连战术细节都被后世研究得七零八落。丁盛深知自己当时只负责一个连,对红军大兵力如何调度完全不了解。倘若贸然出书,一旦记忆和史料有偏差,成绩可能被夸大,错误却永远留档。对比某些回忆录里动辄“手刃百敌”的浮夸,他宁愿把笔收起来。
值得一提的是,两位老人对“资格”一词的敏感,正体现了那个年代军人的共同心理。无论后来职务大小,他们更看重团队战功而非个人荣耀。娄山关只是红军长征中的一站,却给丁盛打开了另一条晋升通道:从基层政工干部转向指挥员,这在当时并不多见。正因为跨界,他比很多出生入死的“老前辈”更懂得谨慎。
疗养院的春日午后显得静谧。谢振华握住丁盛的手,半开玩笑:“老丁,你真的不想写?要不口述也行。”丁盛摇头:“写战史的人多,提名字的也多,少我一个没什么。”未等谢振华再劝,他抬腕看表:“该量血压了,护士要来。”两位曾经的战将就这样结束了一次短暂却意味深长的对话。
后来,昆明日报的那期特刊只刊出一段采访摘录,没有详细的战斗经过,旁人觉得可惜。可在老兵眼里,功劳簿上的名字能少就少,队伍才能多一些骨气。或许这就是丁盛口中“不够格”的真正含义——站得再高,也不占用不属于自己的光环;打得再漂亮,也得对每一颗子弹负责。
2
鼎冠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
